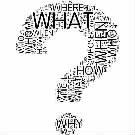
2016年1月6日,北京难得的晴朗天。金融街一栋栋厚重的建筑组成的一条条峡谷中的一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某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吴皖心在她宽大的办公室里端上一杯浓香四溢的咖啡。这位年满45岁的美丽女人在大学本科二年级时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汉娜·阿伦特”,如今在资产管理公司高管的职位上,已经坐了近十年。
“我已经几乎不看哲学书了,我看的是资产管理表。”几年前,记者曾采访过她,她说过这样的话。几年之后,她说的是同样的话。不过,在她办公室镶满了两面墙的书柜中,哲学类图书依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我只是翻翻,没时间细读。”她说。
记者注意到,书柜中一套套的各类思想文丛,很多没有拆封。记者刚进门的时候,她正在看“中投”五大笔加拿大投资失利之后偃旗息鼓撤出加拿大的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中投”每笔投资均达上亿美元……
吴皖心似乎就是这个世代的一面镜子:我们更多地注意资产管理表,很少、甚至不会去关注思想、思潮这类曾经在上个世纪引领了无数人梦想的精神世界的图景。
“现实以及未来的思想风潮,一定是以功利目的为主。”她断言。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句元朝无名氏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楔子”中的话,被吴皖心反复说了4次。在《庞涓夜走马陵道》中,这两句的意思就是:文也罢,武也罢,最终目的都是贡献给皇帝,都要替朝廷出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儒家观念“学而优则仕”的应有之义。
每一个新儒家都扛着一面大旗,旗下应者也不算寥寥。进入2016年,跪拜文化被诟病了,汉服文化被嗤之以鼻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仪式可以招揽拥趸者?佛家的体验式清修,一次砸进去两千大洋,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我们清净了还是更加喧闹了?
哪一种思想可以成为一把万能钥匙,打开通向理想世界的大门?不仅儒家,自由的,保守的,左的,右的,中不溜的,都声称自己有“芝麻开门”的秘诀。
我们在新儒家身上看到过这种景象:缺乏法治?找儒家。缺乏公民精神?找儒家!经济崩溃?找儒家——儒家经典里都有!
非只儒家如此,新道家亦然:我们更自由,更本真,更“心灵鸡汤”……
未来的任何一种新旧思想同样会坚持:我们可以度一切苦厄。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周以恒博士告诉记者:凯迪社区、乌有之乡、新语丝等,这些思想网站的存在充分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活跃与自由,不过它们都过于偏执于一隅,因为包容性差而让真知灼见无法深入人心。还有,一般的思想交流都受限于很小众的圈子里进行,无法跟普罗大众产生关联,缺乏启蒙性的意义。
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在《非洲的污名》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如果你失明了,描述大象难不倒你。如同寓言故事的六个盲人,你可以把它描述成一截巨大的树干,或者一把巨大的扇子,或者也可能是一根巨大的绳子,等等。但事实上,眼睛不会让描述变得简单,反而会使其复杂化。”
但是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大象也只是大象,蚂蚁也只是蚂蚁。无独有偶,写过《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的萨拉马戈写过一篇《大象之旅》,萨拉马戈的“大象”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
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一本影响了中国世纪大变革的杂志《新青年》的百年纪念之年。而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解冻”之后的中国社会迎来了思想解放,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新生机无与伦比。“思潮”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思想如潮水般的冲刷与荡涤,但如今,更多地被时尚的潮流所替代,被功利的追求所羁绊。在思想领域,你只能一睹满目流沙。
当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刚刚在国内出版的时候,多少人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福山这个大厨,终于注意到煤气罐的问题了!这个大厨一直在大秀厨艺,可他一直不想想,没有灶火,他再高的厨艺也是白搭;没有了灶火,这个大厨的菜谱,可以一把火烧了。
我们不去想一想:我们守着一拢烤死人的火,没有粗面,也没有鱼丸……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拥有一种颜色就说自己的画是彩色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仅仅缺乏一种颜色就说人家的世界是黑白的。在大学学了十年哲学的吴皖心说:“我们有点常识好吗?”
踏入2016年,我们不会还是抱持其思相左,其心可诛,其人可杀的心态吧?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说:“容我提醒你,恶只能是人性的。”他反对把理想建立在一种纯道德的观念上。这是对的。你把资产管理表给你的管家或者投资管理人,你不能指望他的道德情操来保证你的资产升值,那是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追责机制的。上百亿的投资一次次打了水漂还可以全身而退,是我们“独尊儒术”不够,还是“黄老哲学”不够彻底呢?
1984年,布罗茨基在威廉斯学院为毕业典礼致辞中说:“我预期你们之中会有潜在的恶棍。”未来的“恶棍”们也许会更多,因为未来的利益会更大,未来的诱惑会更多,而我们可以控制的资源一定会更少。是否应该有人站出来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别做杰克·伦敦笔下跟着狼号叫而成为狼群的一员的那只狗?
数百年的浪漫主义运动是从抗议新时代的第一声呐喊开始的。它以一幅幅对比的形象来捕捉对于历史断层的感受:农村与城市、无知与经验,正在消失的“灵性的牧场”和“放养的黄牛”与那种伴随着“病态的匆忙、满脑子的征税、中风的心脏”的现代都市的病态。卢梭在《爱弥儿》中深情回顾“童年”的“纵情与平静”。华兹华斯、勃朗特、卡罗尔……无数天才们的灵性与批判精神带来的自由主义的光辉,曾经令这个世界大放异彩。
之后,“立足于当下,着眼于现实,深耕于大众,依靠良知与责任”的批判现实主义狂飙般席卷,我们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左翼文艺家承继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让这一世界性的潮流具有了中国特色与风格,启蒙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读书人。这一宏大的思潮几乎已经断流。
1838年,在哈佛这个唯一神教派的堡垒,艾默生在演讲中宣称,这里的人们已经丧失了崇拜的原则,他们的救世主只是一个冻结在石头中的英雄。对此,哲学家卡莱尔的描述更为形象:“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狂热与痛苦在内心激荡……白天再也没有云柱,黑夜再也没有火柱为朝圣者指路。”
而今,我们要回答的,是华兹华斯在《不朽的宣言》中诘问:
幻想的闪光飞逝到了何处?
我们的光荣与梦想又在何方?





